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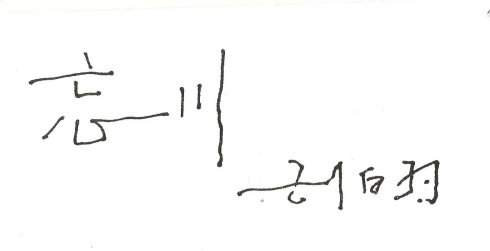
有个传说,天子脚下,若挖土成沟,再填此沟时土便少了很多。
土质疏松了,本应绰绰有余,而与此却相反,谓之“恶土”。但传说毕竟是传说。
护栏的分割下,在两边行人和各种车辆的拥挤下,这条路依然显示得那么宽敞而且豪华。出租车上的刮雨器不停地摆,是因为有雨,才使这条没有土的柏油路显示得那么干净而且明朗。
雨过才能天晴,就像冬天的后面一定是春天。
我祝福着自己,在停车之后,拖着那个连整个人都装得下的黑色皮箱,开始了在这座新城市的生活。
办公室,食堂,宿舍,我穿梭于整个走完才不过十几分钟的报社大院。接电话,拨号码,我重复着那些“早晨好”、“您好”、“谢谢”、“再见”之类的话。
等待。
等待,除了一杯茶水,几张报纸,一支笔和几摞信件稿纸,其他都是等待。电梯要排队,打饭要排队,连去卫生间也要在那位阳总编有些高深莫测地斜视下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悄悄走出房间。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大同小异。
历经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我毫无紧张地接受着每一份从陌生到熟悉。
从我被迫面临这个巨大的人生难题,便开始把白葡萄酒称之为“忘川之水”。白居易曾写诗问刘禹锡说,
“晚来无欲雪,能饮几杯无。”
如今已是初秋时节,我又独身一人,虽无雪景可赏,但一杯浓酒却也说不定能让人感到热切温馨。那个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和沙发,简单到连衣柜都没有的单身宿舍,再加上我这个人,组成一个标准的“五个一”工程。
据说这还是将宿舍楼一层的管理室腾空出来力我专门设置的。楼道里似乎盛满了我从家乡带来的离愁别绪。在这小得可怜的房间,那个显得“无比大”的黑皮箱包容着我刚刚购置回来的各种生活用品。
女孩子繁琐的瓶瓶罐罐散乱地丢在新添置的台灯周围,一张原本不宽大的桌子在摊开的报纸和书籍的堆放下显得不胜负荷。窗子上的两片从来后就没拉开过的窗帘,使紫罗兰色的灯罩下发出的光显得格外亮丽。
我的“忘川”,在无法加注冰块的简陋条件下显得酸涩而浓烈。
冬天就要来了,这是我为自己而设的炼狱!
坐进那张原本就不怎么舒服的沙发,我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雨过后的晴天依然透着一股秋天的寒意,该喝一杯热水。
装满忘川的杯子让我拿着它感觉一直凉到心里。全然找不到古人饮酒留诗的好心情。
倒水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个搁置在瓶瓶罐罐中间的梳妆镜,前面有些散乱却依旧飘逸的长发下的脸,让我判定这个大院里的人一定发现了我并不美丽却十分惹眼的外型。反光的平面把我的思绪牵得越来越远,暖瓶里缓缓流出的热水不知什么时候浸满了桌子的一角。我慌了手脚,想拿开杯子的同时发出了被烫到的尖叫。翻倒的整杯开水洒在右手的手背上,扔掉的暖水瓶和玻璃杯几乎同时落地,在空洞的楼道发出巨大的声响。我捂住右手,眼看着桌边的一摞书一本一本地掉下来,整张整张的报纸在热水的浸泡下慢慢地膨胀。狭小的屋子狼狈不堪。
原本要逃避的一切仿佛又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我想夺门而逃,离开这个离地狱已经很近了的地方,却发现房门早已被推开,而且门口还站了一个人。
“你找谁?”
声音是不友好的!
“您是何小姐吗?
他端详着我。
我故做潇洒地用灼疼的右手拂了一下头发说:
“找我吗?出去说吧!”
“出去?去哪儿?!何小姐……”
他的诧异让我从迷蒙中转向现实,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没在意过这位陌生客人的感受。
我的脸一定红了,若大一个城市我能去的地方在哪里呢?
“里面……里面太狼狈……我……想到外面去透透气。”
他环视了一下屋内的景象,善解人意地递给我一把钥匙:
“外面有辆红色的车子,相信你一定找得到,先到里面去坐一会,我来帮你把这里收拾一下。”
我的脑袋里空空如也,顺从地接过车钥匙,我果然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的车子。我把坐位放低,躺进这个比房间里的沙发还要舒服很多的位置里面。车上有些冷,我发现自己只穿了一件黑色的薄毛衣。左手的四个手指和右手的整个手背都火辣辣地疼。正要下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拿着我的风衣和手提包从楼道里走出来。我这才注意到,原来他有很高的个子,很高的鼻子,很普通的装扮和单眼皮却很有神的眼睛。
我被动地接过风衣和提包,没等我说声谢谢,他便彬彬有礼地为我关上了车门。盖上风衣,我感觉温暖了很多。发动车子的时候,他一直在偷偷地看我。我装做若无其事地将提包扔进后座,但还是很不自然地才把眼睛闭上。
反正自己的形象已经狼狈透顶,何必再去摆出一副淑女神态呢?这么想着,一星期以来谨小慎微的生活使疲惫从四周包围过来。车子开得很稳,迎面能感到不断吹来的暖风,灼痛的手慢慢恢复,一切好像都沉静下来,我也真的好像要睡着了。
正要沉沉睡去之时,我的脑袋里突然警惕地反应出:
这个人是谁?
他找我干什么?
他要带我去哪里?
“停车!”我几乎在喊叫。
从认识这个人以来,我一直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简直不可思议,倒霉透顶!
“你为什么知道我?”
“你是谁?”
“找我干什么?”
“要带我去哪里?”
在急刹车的响声之后,我一连串地问他。
盯着我看了几秒钟之后,他才从容地回答;“别着急,小姑娘,我是张处长的学生,是他让我来看你的。在我来你这儿之前,刚刚跟他通过电话,他说你的信他已经收到了。你在信中说还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和电话号码,张处长说他有些担心,要我到报社这边看一下。我本来是路过这里,想先打听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你。”
“而且还这么狼狈!”
我接着他的话说,眼前浮现出张处长这位好心肠的老先生的样子。记得我坚持离开单位之前他就讲,“我在北京教过书,到时候我让以前的学生去看你。”
他似乎预见到像我这样一个被宠惯的女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踽踽独行是多么寂寞而艰难。
“我叫秦予,给予的予。你别紧张,现在才七点多一点,我先送你去医院包扎一下。”
他看着我那双已经起了白泡的手。
“张处长说你钢琴弹得很好,我希望能早一天听到。”
说着他又发动了车子。靠直了椅背,我开始注意马路两边的建筑物,城市的夜景几乎都是由霓虹灯和广告牌构成的。我下意识地叹息。
“要音乐吗?”秦予征求意见地说。
“可以!”
我的大小姐脾气又开始了。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从医院出来后我真诚地感谢他。
“没什么,是张处长的电话及时。他原本的意思就是让我关照你的。”
“可我今天实在是丢人……没面子。”
我打心眼里就是这么想的,他听后却只是笑笑说:
“小姑娘,这有什么可丢人的!”
“小姑娘!”这个称呼应该是我极为熟悉的。感谢祖父的远见卓识,我还不到六岁就被送到了学校。无论在哪里似乎我都一概被冠以一个“小”字,可他的口气似乎刚才是在包容一个小孩子。
“秦先生,我是属兔的,已经二十二岁了。”
我强调着“已经”两个字。
“那你是小兔子,而我却是老兔子了。”他说。
“我已经三十四岁了,你还不算是小姑娘吗?”
“那你也最多是只大兔子,还不能算老。”
我开郎的天性让环境变得宽松了很多,他的长者风范让我感觉像是跟张处长待在一起,毫不掩饰,也毫无防范。很快忘记了自己刚刚还在为上药而眼泪汪汪,也忘记了跟他认识才不到两个小时。
“你刚才的样子,连十二岁都不如。”
我知道他是故意在逗我,便装做没听见似的哼着歌,等他的车子驶出了车位才说,“为了感谢你在我落难时的英雄之举,我说个故事给你猜。”
“你那些小孩子把戏,我肯定猜不出的。”
“真搞不懂,你的心态怎么会这么未老先衰,张处长可不像是教考古的。”我没理会他那份不应有的沉重,继续说,“有一个农夫去赶集,买了一只羊,回家以后想了想又回去买了一只,你说为什么?”
可能是为了不让我扫兴,他很认真地说了几个答案,但终于还是没能逃出我问“为(喂)什么”的埋伏圈。在我告诉他答案的时候,他笑得连车子都开不成了。我乐不可支,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
再次发动车子的时候,他笑着说:“喂草,好吧。不但羊要吃草,兔子也要吃草的,你不是变相给我提意见吧,我还没顾得上喂你这只小兔子呢?”
“天那!我打的饭真的忘记吃了。”
“你是我在国内见过唯一一个独自喝酒的女孩子。”
没想到这件事竟然会留下这么大的后遗症,无论如何,我是不愿让任何人窥探到我的内心世界的。好在他没做继续探讨,只是用刚上车时的那种眼神看着我。
“那边不是有好多餐馆吗?干嘛不停车。”
我特意岔开话题。而且在他的提醒下,我确实非常非常地饿了。虽然出来这一星期以来忘记吃饭已是经常。
“别着急,我带你去一家有好多火腿蛋的地方。”
他的话忍不住又让我脸红。“火腿蛋”,我想起在开葡萄酒的时候,感慨报社食堂的菜总是加京酱而画饼充饥似的在盒子的四面写下了“火腿蛋”、“龙虾”、“熏鱼”、“忘川之水”。
“我本来以为可以为自己勾勒一个社会主义。”
今天我还是第一次感到很不好意思地为自己做解释。
“放心,我保证把你喂饱,把你的乌托邦变成现实!”
几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在一家西餐厅落座。
他理所当然地要了“火腿蛋”、“熏鱼”、“龙虾”,我饿得已经开始往赠送的面包上抹黄油。没面子的事反正都做尽了,我准备风卷残云。等到菜都上齐了,他终于忍不住问:“兔子小姐,忘川之水是什么?”
我塞了满嘴的面包,口齿不清地说:
“白葡萄酒加冰块”。
“我真怕你要我到外星人那里给你找水呢!”
我咽下面包,喝了一口及时端上来的“忘川”,神情严肃地对他说;“我可没逼你做什么!”
说完之后又有些内疚,毕竟自己没理由来埋怨这样一个有心人。他不但没生气,反道说:
“实现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嘛!”
他的话实在让我感动,从认识他到现在,我真的相信他一切都能做到。回到宿舍已经是点左右了,他给我留下一张名片,还在背面写下了住宅电话。
“有需要随时找我。”
简单明了的一句话,让我在这个偌大而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一棵无忧树。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真的以为小海螺的神话故事发生了。
“我真的不能相信,你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我这个如此之乱的房间打扫得那么干净。”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打电话向他表示谢意。明片上有关一栏的号码很繁琐,我直接拨了他的手机,通话的时候有电话铃声在不停地响,他的语气也变得严肃了很多。我知趣地很快收了线,因为星期一上午一上班是大家都最忙的时候。而我也知道,来了一星期自己不可能再在一大堆自然来稿和接公事电话中沉闷下去。
“小何啊!”
临近中午的时候外面的阳总编终于打破了我每次路过他办公桌前的欲言又止。我答应了一声,走出房门。我的办公室因为暂时无法安排而被指定在阳总编的休息室。我所在这间屋子的正门已上了锁,而另外一扇门与阳总的房间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我进进出出都得路过他的办公桌,甚至连电话都是连在一起的。
虽然是休息室,但办公设备却一应俱全,都按报社总编的待遇:直拨电话,内线电话,高背椅,老板桌和书架对面的一张长沙发,一把带轮子的真皮转椅。说是休息室,还不如说是个不伦不类的接待室。我顺手拿了把暖水瓶,想帮他加点水。
阳总受宠若惊地从板椅上弹起来:
“不用,不用,这些事情不需要你来做。”
中国人的工作习惯原本是靠一代一代往上熬。年轻一点的自然要为年老一点的,特别是领导级的“同志”多做些端茶倒水的事情。以我参加工作一年多来的经验,女“同志”们大多认为理所当然,并且还有点正中下怀的味道,而男“同志”大都客气得有些不自然,反而怜香惜玉,不肯“重用”。对于这种光荣传统,如果上升到人与人的互相帮助,敬老爱幼这个标准,倒不会有损于任何人与生俱来的高傲。况且在任何氛围,我这种举动最多只是初来乍到时的形式主义,毕竟我从没把自己当成是勤杂小妹。
这么想着,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软椅上。其实,这种谈话早在几天前就该发生了。
“这里还满意吗?”
他的问话让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来打工的,反到像个被接待的客人。说实话,这所谓的打工似乎高级了一点,我却并不想在这样一间办公室里办公。虽然这么想却还是点了点头。
他用一只手敲着桌子,若有所思地说:
“看过你的简历,对你以住的工作成绩很欣赏。你为一家集团公司在募捐方面的商业性论述还获得了宣传部门的大奖。报社能来你这样的人才我很欢迎!
“我们这张报纸主要跟经济挂钩,很适合你。我考虑了一下,仅仅让你躲在办公室里编些副刊的稿子太可惜了!而且文艺部又满员,没有办公的位置,跑来跑去也不方便,干脆你就留在这里办公,多为社里做些对外的工作吧!”
我的脑子开始飘乎到很远的地方。我经常有个习惯就是走神,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听得清老师讲的每一个字,却不知其意;在一大堆人中跟着喜怒哀乐,灵魂却弄不清被牵到了哪里。
当老总的最擅长滔滔不绝,我看似谦逊地点着头。他抽烟的姿势让我想起了吴庆凡,这个让我走进这座炼狱的家伙。
当我故做恭敬地双手去接他递过来的文件时,他发现我两只手上都缠着纱布。
“好了,既然你受了伤就回去休息吧!我看你精神也有些不集中。”他拿出一把钥匙,“明天上午你可以走前面那扇门,下午我会让人来帮你改造一下工作环境,这间休息室早该利用一下了。”
我们结束了谈话,得知我的手被烫伤,他催促我赶快回宿舍休息,并且叮嘱我收好自己的东西,以便下午有人来改造房间。他跟我这个典型的北方姑娘站在一起显得特别矮小,聪明绝顶的头上已经开始地方支援中央。算是个传统的老总形象吧!不无好感也不无厌恶。难为这个南方老头竟主动出让了他的休息室。但或许,是于珍的承诺。我的脑袋里略过一丝阴影。
于珍,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是不是我到了三四十岁以后也会变得那么狭隘、自私、可怜、卑劣呢?不是所有三四十岁的女人都是变态狂的,至少我不是。
“阿弥陀佛!不!上帝保佑……”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走向电梯。
“几楼?”
原来里面还有一个人。
“楼”
我漫不经心地。
“你走路的时候还会念经?”
我瞪了他一眼,跟本不想跟他谈话。六楼到一楼原来需要这么长时间,早知道还不如走楼梯呢!他一直盯着我看,肆无忌惮而且毫不介意我的反感。
我走出电梯时才正眼看了他一下,原来他长得还蛮英俊的,只是头发有些长,有点像唱摇滚的痴迷青年。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却有股子傻气。
坦然地接受一切,这对我应该习以为常了。(一)
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贝壳里。“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哼着苏芮的歌,我坐在这个名副其实的“蜗牛的家”中间。经过秦予昨晚的一番体制改革,它已经大有变化。我的瓶瓶罐罐有序地排列在梳妆镜周围,浸湿的报纸已经晾干,我把它们放在摞得很整齐的书和画册上面。
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里可以静静地写点什么。即使在家,现在也只是一个人。我想起了我的母亲,那个曾经在政治与家庭的纷乱中走过的优秀女性,在她的女儿二十二岁的时候,她才得以回第一次娘家。还有父亲,他是个标准的老古董,第一次去晋见丈母娘就把我这个独生女儿置之不顾了。
我知道把我托付给了张处长,他们俩真的会很放心。可现在弄得我们俩还不知道是谁照顾谁呢!
“你们去台湾这三个月,家里的一切都不同了。”
确实该给他们写封信了。虽然我知道张处长会写信告诉他们,我是怎样莫名其妙地突然决定要来北京发展。
离家的人往往在最困惑、最无助的时候想起那个自己曾经最不经意、也最不珍惜的地方。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是秦予,他提了一个电热瓶盒子。经过昨晚的相处,我们像老朋友重逢,完全不拘礼节。
“奖励你昨天晚上战功累累!”
放下手中的电热瓶,他变魔术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方盒子。我迫不急待地打开,里面是一只很漂亮的杯子,上面印有两只可爱的小兔子,一只正拿着萝卜呲牙咧嘴;另一只则躲在蘑菇做的房子下面托着腮冥思苦想。中间有一句英文:
“!”
我高兴得爱不释手,指着图案编故事给他听。
“小姐,我可不是来听你编故事的。”他边说边拿起我的风衣和提包,“走,我先带你去换药。”
“不,我不需要小题大做。”
没等他说完,我就反驳。
“必须去,我可不是只为请你吃饭才来的,你知道我有多忙吗?”
他的责任感让我无话可说。
换药的时候连医生都认为大可不必再劳师动众地缠什么纱布,而他却依然认真得要命: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么嫩的皮肤,可能会留疤。”
从医院出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命令似的语气让我一直都在沉默。昨晚猜谜语故事的随意和融洽减少了很多,我孤傲冷淡的潜质在不自觉地发生作用。他对我性格的两面性显然适应了很多,不再表现出诧异和惊奇。
“还要吃薰鱼和火腿蛋吗?”
他语气里已经没有了“必须”两个字。
“去郊区吃点特别的东西好吗?今天下午我放假。”
说完之后我又马上感到失言。
“何风啊何风,你放假不等于全世界的人都不用工作啊!”
不知道我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坏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掉。甩了甩乱糟糟的头发,我径自往车门旁走去。
“去吃猫耳朵之类的老北京风味,行吗?”
他走上前去为我开车门。
“我可不是只为请你吃饭才来的,你知道我有多忙吗?”
我学着他的语气说。
“,只要你有时间”
他说了句半洋不洋的话。
“好在我还是个老板,下午不去写字楼我的手下都会感谢你。”
他的幽默换来了我的好心情,我又开始给他猜那些脑筋急转弯的题目。谈笑间,车子也七弯八转地来到一个小胡同,他突然停了车。
“你知道老北京的传说吗?”
“传说?!”
我有些不解,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是一排排老式建筑,或者是以前的什么王府,要不然就是皇帝的行宫或花园什么的。这是一个隔市区有些远的地方,没有了大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厚重的矮墙,古典式的人字型屋顶及隐约可见的画梁雕栋,让你感觉比站在高楼大厦之前还渺小。那栋矮墙似乎伸手可攀,但由它包围起来的四角天空却充满了不可逾越的神秘。
我弄不清北京那么复杂的地形,却不想问他这是哪里,以免影响他的思绪:
“老北京人传说,古代天子脚下是恶土。恶土是什么知道吗?在这里拿铲子挖个沟,然后再填起来,本来挖开的土质变松了,填沟的时候土一定会绰绰有余。可就是因为是恶土,还用挖出来的那些土,这个沟却填不满了。”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也沉默不语。直到我们去一家名为“感恩”的餐馆吃饭时他才开口。
“吃中国菜不要忘川之水了吧!”“”
我学着他的样子说英文,使不和谐的气氛再次离我们而去。他为我要了各种北京的风味小吃,我却没了昨晚的好胃口。不仅沉浸在“恶土”的传说中,还急切地想尝试一下他的讲述是否真的只是传说。再次路过那个胡同我不无感慨地说。
“以前只是说覆水难收,现在连覆土也难收了!”
“人有时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付出很多难以收回的东西,留下很多难以弥补的遗憾。是惩罚,或是赎罪。总之它越想越深奥。”
也许是他不良心情的影响,我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受不了车上沉闷的气氛,我胡乱用词地说:
“人间自有真情在,何须愁白少年头。”
“我已经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了。”
他说着,放开了音乐。车子周围很快弥漫了一首比语言更让人心动的歌:
相忘总难忘!风雨倾城泪满襟!欲诉无处寻谈者!
又过今夕,
何年是佳期?把宽容留给世界,把平淡放在今生,让人字相互扶持,用笑颜写意春秋。莫言愁、莫道老、莫将一世枉过了,说一声小心、珍重,一切都变得生动,
爱本很小,是个图形。
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是细细品味着歌词的深意。
“噢!我已经到了,谢谢你这首这么好听的歌。”
我走进报社大院。这个在我一生中原本不应走过的地方,会有生动可言吗?“小心、珍重”。是啊!小心、珍重。
当我再次步入办公室的楼道之时,发现阳总办公室前面的那扇门上方已挂了一个“联络部”的牌子,而且门上还贴了我的名字和一个小型信箱。我用阳总给我的钥匙开了门,我不得不承认那份从心底里感到的舒畅和惬意。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大都市,我从来没奢望过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个气派而宁静的办公环境。
跟阳总办公室相通的那扇门已经上了锁。我知道这纯粹是在避中国人的那种嫌,因为从我到这儿来的第一天,来阳总办公室的人都会站在这扇门口冲阳总诡秘地一笑,然后小声地说上一句“金屋藏娇”之类的话。方块字的演绎功能之大是每个中国人都体会极深的,虽然我一直漠视这种误会但还是感到极不自在。
以我来这里一星期的了解,这家报社是决不缺人的。一定是于珍动用了她那位当过大人物的父亲,现在这样的安排大概就是她想让我乐不思蜀的计策。那我算不算是因祸得福了呢?
我拿着阳总给我的文件,步入这间暂时属于我的办公室。
笨重的老板桌和高背椅已经被搬走,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小巧的公文桌,一边是新放置的电脑,一边是以前的两部电话,对面是原先的那个真皮转椅,长沙发依然没有撤走,所不同的是书架已腾空了大半,除了必要的工具书,他们给我留下了一大半的空间。我坐进那张可以左右转动的低背软椅,最大限度它可以让我斜对着背后那扇几乎落地的窗子,只是外面除了高楼林立,没有任何湖光山色。
“联络部”,我真的有能量让这家报社为我而成立一个部门吗?我突然有一种畏罪感,整件事情我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受益者呢?于珍,她有必要为了女性的一点神经质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望着窗外路面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想着那个有关老北京的传说,我根本没注意到对面的转椅上坐了一个人。
“漂亮一点的女孩子是不是都有些深不可测?”
我收回视线,发现是昨天在电梯上看得我有些发毛的那个痴迷青年。
“先生,您知道这不是电梯,进屋的时候应该敲门。”
他依然毫不生气,走回到门口,他彬彬有礼地敲了敲门。
“请进!”
“可以坐下吗?”
我点点头表示可以。我发觉他的摇滚式发型已经修理过了,而且穿了一套很讲究的西装。
“我叫李云生,是发行部的,阳总交代说要我先带你熟悉一下报社的情况。”
“那你是我的上司了,有什么工作请指教吧!”
我依然有些不友好。
“我想,现在应该称你为何记者才对。”
“不用了,我叫何风,你可以叫我的名字。是风雨的风。”